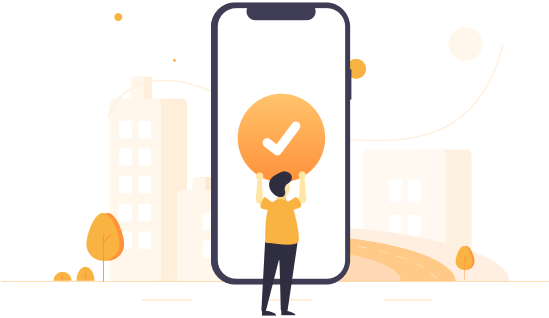来源:财经国家新闻网
2013年12月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闭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等规格、交叉套开,重要性不言而喻。
“城镇化是当前和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郑新立在我国经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他亦是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
在郑新立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涉及的改革达300多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难度最大的。此外,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党的文件里,第一次对生态文明体制系统地做了阐述和部署。
就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思路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具体部署,郑新立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几个小时的专访,郑新立思维清晰,语速飞快,能清楚准确地说出一连串的重要数据,对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他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但也时时透露出对农民工、留守儿童、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人文关怀。
农地改革关乎城镇化成败
《财经国家周刊》:刚刚结束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思路定调,你对会议部署有怎样的解读?
郑新立:城镇化是当前和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如果未来10年到20年间城镇化率保持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将有一千万以上的农村人进入城市,为此增加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足以拉动未来经济较快增长。
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0%,如果20年后再提高20%,30%人口住在农村、70%人口住在城市的城乡结构基本就定下来了,我们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也就基本实现了。
《财经国家周刊》: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6大任务,其中一个任务是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对此你有怎样的想法?
郑新立: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镇化都是循着一条人口和资源不断向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聚集的道路推进。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以后不能再搞了,城市发展到上千万人口就是“灾难”。
未来城镇化将分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形成三大都市群,这三大都市群在未来十年内经济总量将超过2万亿美元,进而超越纽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
第二个层面是以省会为中心形成“次区域城市群”,目前发展比较好的有四个: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圈;以成都和重庆为两极的成渝城市圈。未来在次区域城市群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将靠城际高铁连接起来,都市群和次区域的城市群也通过高铁连接,大大小小的城市形成半小时生活圈、一小时商务圈,形成同城化、一体化的发展。
第三个层面则是以县城为中心、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础的城镇化局面,吸引更多人向中小城市分散。目前,在苏南、浙江、珠三角等地已经有了现成案例,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形成了半小时生活圈,比如浙江安吉,老百姓在县域二三产业从业,但还居住在农村。房子在农村都是依山傍水,周围竹林环绕,非常优雅清静,生活工作很方便很现代化,农民就不需要往城里跑,这就叫就地城市化。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城市化,像德国是一个城市化很成熟的国家,但德国人讨厌大城市,67%的德国人居住在小城镇,一个小城镇10万人左右,主要依托一个工厂或一个银行。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就地城市化,还是有很多农民工需要到城市落脚,会议提出了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那该如何保障进城农民的权益?
郑新立:我们有2亿多农民工,未来要在城里市民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地方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涉及的改革达300多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难度最大的。
《决定》为农民工在城里扎根提供了三个条件。第一是耕地转包。农民将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出去,别人搞规模化经营,效率高,又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000061,股吧)。然后农民到城市打工,工资加上土地转包费,就容易跨入中等收入家庭行列了。
第二是出让宅基地。现在中国土地最大的潜力是宅基地,城乡建设用地一共22万平方公里,包括县城和城市以上的大中小城市占5万,宅基地却占17万,农村一个人的建设用地面积是城市的3.5倍。宅基地这么大的资源一直没发挥作用,三中全会把这个金库打开了。农村宅基地流转改革,可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满足城市化需求,城市房价亦自然下降。
第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可同地同权同价。过去农村建设用地是先征地变成国有,搞一级开发,再进行招拍挂,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无论是集体收入,还是分给老百姓,都是一个大红包。
此外,我国有3~4千万留守儿童在农村,父母离开他们去城市打工,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很多创伤,如果农村的宅基地可以卖掉,他们在城里有了房子,把孩子接到城里,让他们全家团聚,这是一件大善事。我们各项政策应推动这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但农民工进城至今各方认识仍不一致。不赞成改革的一方担心,“万一进城农民失业了怎么办,他们也不能重新回到农村,会不会沦为印度、巴西等国城市中的贫民,成为城市解决不了的问题”。
郑新立:这种担忧没有必要。中国的农业和美国加州的农业相差不止100年,中国过去在理论上、政策上,长期鼓励让农民躺在自然经济、小规模经营的温床上,还要维护农户在农村的经营主体地位,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只种6.4亩地,永远难富起来。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不会倒转,第一代农民在城市能找到工作,第二代本事会更大,在城市上大学,至少读个中专、技校,竞争力会超过第一代,他们不会再回农村了。农村2.8亿的劳动力,只需要留下8000万种地便绰绰有余,其余2亿农民可以进城。尽管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规模已趋于饱和,但服务业容量还很大。中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比例只有36%,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2%,因此未来两亿劳动力到城市能做什么?就是搞服务业。不用再纠结农民工失业问题了,因为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调查,目前农民工失业率只有6%,但大学生失业率已经到30%了。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成员,“重庆地票”的农村土地改革模式会不会更普遍被推广?
郑新立:我和黄奇帆在一个起草小组。重庆的土地制度改革搞了四年多,它是把重庆郊区分散的、零星的建设用地,包括原来农村的板砖厂、窑厂、村镇企业、宅基地等进行土地复垦,这些新增的耕地经国土部门丈量后,发地票给农民,农民拿地票去市场交易,需要建设用地的投资者也到这个市场去买地,然后由城市规划部门统一调节规划使用。
重庆如此试验了四年,产生了四个效果。第一是卖地的收入一共200多亿,农村集体拿了15%,农民个人拿了85%,有近二百亿卖地的钱装到了农民口袋里;第二是重庆市不缺建设用地,所有到重庆投资的企业都能实现项目落地;第三是四年时间内,这些零星的建设用地,不仅满足了新增建设用地的需要,还新增了7多万亩耕地;第四是形成了一个土地交易价格,20万元一亩,银行以每亩20万的抵押向农民提供贷款,一共贷给了农民70多亿,支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
《财经国家周刊》:这些经验对其他省份是否有借鉴意义?
郑新立:比如河北省。河北省与北京市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但是河北省没建设用地。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跟我说,河北很想接收过来,但是河北建设用地严重短缺。我建议他去把重庆建设经验学过来,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生态文明体制首次破题
《财经国家周刊》:你参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全会对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在你看来,这些部署和以前有哪些不一样?
郑新立: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元一体化的五个体制里面,其他四个体制中央都专门开过会,做过决定和部署,在党的文件里,第一次对生态文明体制系统地做了阐述和部署,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破题。
《财经国家周刊》:文件中关于生态文明体制的具体部署,你有怎样的解读?
郑新立:第一是《决定》中提出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就是包括河流、湖泊、海洋、山地、草原等将来的产权都要明确责任主体,由这个责任主体对自然资源维护负责,而且要实行离任审计制度和自然资源损害的终身追究制度。这非常重要,是第一次提出来。
第二点就是提出建立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通过“谁污染谁付费”和第三方治理形成一个机制。“谁污染谁付费”是一个新提法,过去我们一直提“谁污染谁治理”。但“谁污染谁治理”很难真正得到落实,一直流于形式,实际上变成了谁要是治理了,谁就吃亏,谁要是不治理,谁就赚钱。
比如一个60千瓦的发电机组,火电厂一年的脱硫脱硝除尘成本需要8千万元,如果企业偷排或者装一个假设备,成本就变成企业收入了。过去我们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检查来了,企业赶紧把设备开起来,检查的一走,就把机器关上,或者是白天开、晚上排污,这个实践证明“谁污染谁治理”不行。
未来如果改成“谁污染谁付费”,企业只要排放了污染物,无论是气体、液体还是固体,核定一个标准你要交费,然后由政府通过招标,选择拥有先进技术、设备和经验的企业来治理,保证把最好的设备装上去,保证它24小时开起来。
起草的过程还有一个小插曲。原来起草的文件写的是“试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但最终在全会上讨论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这项工作已经试行有段时间了,应该改成“推行”。就改了一个字,我们未来在治理雾霾等问题时,相关工作可能要提前好多年。
《财经国家周刊》:一讲到环保不少人就提到必然影响经济增长,发展仍是未来中国的重要任务,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郑新立:之所以一讲到环保就提到必然影响经济增长,是因为我们过去还没有找到一个共享性的公共产品市场价值补偿机制,说白了就是新鲜空气人人都在享受,它不像别的商品一样要通过市场购买,如果一个企业为新鲜空气做出贡献,有了投入,但这个投入如何产生利润?如果投入不能取得回报,光是靠企业觉悟,那肯定是干不成的。现在就找到了这样一个机制:“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
《财经国家周刊》:在你看来,环保产业是否将成为一个新的投资热点?郑新立:对环境生态的投入,同样可以产生GDP,可以产生利润,可以增加就业,这样就将形成环保产业的庞大市场。包括脱硫脱硝、除尘、水污染治理等专业技术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能创造出可观的税收及就业。
今年以来,在华北、华东地区连续出现的大面积雾霾天气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忧虑,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大气的污染,在我们首都北京肺癌的死亡率已经上升为第一位,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这样的严酷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应该利用市场机制,拉动环保产业的发展,使环保投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目前,环保部正抓紧制定《京津冀地区联合治理大气污染行动计划》,一共十条,措施非常有力,这十条措施出台后可能对环保投入形成一个热潮。
《财经国家周刊》:在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藩篱需要破除?
郑新立:我认为首先要破除三个落后理念。第一,要破除强调环境保护必然牺牲发展的观念。环境保护和发展是可以统一的、协调的,而且环境的优美为人类创造一个适于居住的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和内容之一。
第二,要破除“煤电便宜,所以要重点搞煤电”的观念,忽视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现在煤电的成本看起来1度电只有4毛多钱,风电、太阳能1度电要8毛到1块,但我们把环境成本、人的健康成本、医疗成本、人们寿命缩短的成本也全部算进去,那么煤电的成本可以说已经接近或者是相同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再也不能用这个观点指导经济工作了。
第三,要破除认为“环境治理可以慢慢来”的观念。有人认为英国治理雾霾用了50年时间,我们着什么急呢?我认为在3-5年内,治理雾霾可以取得明显的成效,很多人说不可能。英国当年治理雾霾还没有治理的技术,现在世界上治理大气污染,脱硫、脱硝、除尘的技术都是现成,而且绝大部分设备国内都可以制造,现在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原来缺机制,现在机制也有了,我相信治理大气污染在3-5年见到成效是有可能的。
郑新立简介
郑新立,1945年2月出生,河南唐河县人。1969年8月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曾在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计委工作,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四次参加三中全会(第十四届、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文件起草。